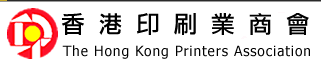在全球造紙產業的版圖上,一場深刻的變革正以冰火兩重天的姿態上演。東方,特別是中國,產業巨頭們正以一種近乎「自殺式」的姿態,掀起百億級的產能「加法」狂潮;而在西方,歐美傳統豪強則在進行著一場理性的「減法」運算,持續關廠、裁員、收縮戰線。這一增一減之間,並非簡單的市場冷暖差異,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生存法則的激烈碰撞。中國的“加法”更像是一場以未來市場主導權為賭注的殘酷“清場賽”,而歐美的「減法」則是在成熟牌局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「精算術」。
中國的「加法」:以擴張為武器的生存之戰 一個巨大的悖論正籠罩著中國造紙業:一方面是產業陷入「越擴產越不賺錢」的惡性循環,2023至2024年間,新增產能超千萬噸,而需求增速僅為1.5%,導致價格戰與低開工率成為常態;另一方面,頭部企業的巨額投資卻從未停歇。
這並非非理性的狂熱,而是一場關乎生死的「軍備競賽」。其核心邏輯不再是分享增量市場的盛宴,而是在存量搏殺中,透過極限擴張來贏得終局的入場券。
巨頭領銜,建構「林漿紙一體化」的成本壁壘。在這場戰爭中,「林漿紙一體化」是最核心的戰略武器。擁有上游紙漿供應的企業,才能在慘烈的價格戰中掌握成本優勢,立於不敗之地。
玖龍紙業的佈置堪稱典範。在廣西北海,透過產線調整,最終將形成漿紙總產能高達910萬噸/年的宏大佈局。在重慶,又斥資60億元建設「漿紙一體化」智慧工廠,以70萬噸綠色製漿工程直擊原料自主的產業痛點,其目的正是建造起無人能及的規模與成本護城河。
太陽紙業在廣西的林漿紙一體化三期工程雖有調整,但其戰略核心愈發清晰:投資71.8億元,將原木漿生產線升級為30萬噸/年的高純度天然纖維生產線,聚焦高附加價值產品,實現從傳統造紙向生物質精煉的轉型。這既是技術突圍,也是在主戰場之外開闢高利潤的戰略側翼,以支撐其在白熱化的常規品類競爭中持續投入。
五洲特紙在湖北、江西兩省的規劃總投資額超過400億元,其中湖北漢川、武穴和江西湖口的項目均是旨在打通漿紙產業鏈的重大佈局;山東世紀陽光紙業在日照投下202億元,建設以紙代塑項目,規劃年產量為265萬噸,建造80萬噸竹漿和120萬噸高性能紙基新材料項目,深耕特種紙領域;華泰集團聯合玉林市政府、聯合華友,簽署總投資280億元的合作協議,其中160億元用於建設沿海林漿紙一體化項目……這些項目共同的指向,都是通過向上游延伸,將產業鏈自己的命脈牢牢,將在產業手中。
然而,這些動輒百億的投資案,表面上是企業雄心的展現,其實是「大魚吃小魚」的進攻性武器。在產業下行期,巨頭們透過主動擴張,加劇市場供過於求,將產品價格打到成本線以下,其目標清晰而冷酷:以短期的利潤損失為代價,將那些沒有上游原料優勢、資金實力薄弱的中小企業徹底拖垮,加速行業洗牌,最終實現市場出清。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「絞殺戰」。
歐美的「減法」:聚焦利潤的理性收縮 與中國的殘酷內捲形成鮮明對比,歐美紙業巨頭的「減法」運算顯得冷靜而務實。其市場早已完成整合,形成了穩定的寡頭格局,因此,企業的核心目標是優化資產、提升效率、回報股東。
併購驅動,優化全球網路。史墨菲卡帕與維實洛克、國際紙業與得斯瑪等世紀併購,其首要任務便是對合併的龐大資產進行優化整合。史墨菲維實洛克今年已在美國和德國關閉多家工廠,合計削減超過50萬噸產能。國際紙業更是大刀闊斧,不僅關閉了路易斯安那州年產80萬噸的箱板紙廠,更啟動了一系列涉及紙廠、回收廠和紙箱廠的關停計劃,影響範圍遍及全美多個州。
市場萎縮,多品類產能同步削減。包裝紙領域,美國喬治亞太平洋公司永久關閉喬治亞州的箱板紙廠,影響535名員工;加意包裝集團也宣布關閉其位於俄亥俄州的塗佈再生紙板廠;格雷夫至少部分關閉其下屬的4家工廠,包括馬薩諸塞州菲奇堡的箱板紙和非塗佈再生紙工廠。
文化紙與特種紙領域, 芬蘭的芬歐匯川透過關閉德國和芬蘭的兩家工廠,合計削減57萬噸紙張產能,佔其總產能的13%。芬林紙板多古紙廠的生產已於6月17日正式畫下句號,當天,工廠內的BM1紙機也完成了最後的使命,宣告關閉。Sappi歐洲在芬蘭洛赫亞的柯克尼米工廠評估永久關閉其2號紙機的可行性。先前已經啟動了對德國阿爾費爾德工廠部分資產重組的磋商程序。 。瑞士的珠光紙業則因市場嚴峻而裁員。Pixelle特種紙關閉俄亥俄州一家造紙廠的行動,影響員工多達800人,凸顯了企業轉型中的艱難抉擇。
歐美的「減法」行動,是企業在市場成熟、需求(尤其是文化用紙)結構性下滑、營運成本高企以及股東回報壓力等多重因素下,為求生存和發展所採取的理性選擇。其目標是透過產能出清,改善供需關係,進而穩定價格,提升整體獲利水準。
不同生存法則下的殊途同歸 中國造紙業的「加法」與歐美同行的「減法」,表面看是發展階段與市場環境的差異,但深究其內在邏輯,則是在不同生存法則驅動下的殊途同歸——兩者都在通過各自的方式,加速行業的集中與整合,以求在未來的市場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。
表象之下:中國式擴張的「生存悖論」 防禦性擴張:不進則退的「囚徒困境」。正如業內人士所言,這是一種防禦性策略。在產能過剩的紅海中,任何一家企業停止擴張,都意味著其市場份額將被對手迅速蠶食。為了不被淘汰出局,即便是飲鴯止渴,也必須跟上擴張的腳步。這已不是為了成長,而是為了生存。
進攻清場:「大魚吃小魚」的終極遊戲。更深層的邏輯是,擁有資本和產業鏈優勢的巨頭,正在將「逆週期擴張」作為武器。它們的目標非常明確:在產業下行期,利用自身「林漿紙一體化」帶來的低成本和規模優勢,故意加劇市場供應過剩,壓低產品價格,從而拖垮那些依賴外購紙漿、成本高昂、資金鏈脆弱的中小企業。這是一場以短期利潤為代價,旨在清除競爭對手、實現市場出清的「絞殺戰」。
策略本質:終局思維下的市場整合 從這個角度看,中國頭部紙企的「加法」,本質上是一種高成本的准入券,用於購買進入行業終局的資格。目前承受的虧損和低利潤,是為未來市場格局優化後,取得更高定價權和市佔率所需付出的代價。其戰略核心是「內部整合」,透過慘烈的價格戰和產能競賽,重塑國內市場由少數寡頭主導的穩定格局。
與之相對,歐美企業的「減法」,則是「外部優化」的邏輯。它們的市場早已完成內部整合。因此,其當前策略是剝離全球範圍內效率低或不具競爭力的資產,將資源聚焦於高利潤的核心市場和業務,以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。它們是在一個已經成形的牌局裡,透過精算來優化自己的每一手牌。
總結而言, 「東增西減」的現象,揭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競爭哲學。歐美巨頭是在一個成熟的、規則明確的棋局裡進行“精細化運營”,追求資本效率和利潤。而中國巨頭們則是在一個混亂的、尚在定局的戰場上進行「生存之戰」,它們的目標是活下來,成為製定規則的人。
因此,中國紙業的投資熱潮,並非單純的非理性擴張,而是一場深刻且痛苦的產業結構性重塑。這場以產能為武器的戰爭,將以大量中小企業的退出為終點,最終鍛造出少數幾個規模空前、擁有全產業鏈控制力的超級寡頭。當這場內部「戰爭」塵埃落定後,這些浴火重生的中國巨頭,將在全球舞台上展現更強大的競爭力。 |